她第一眼看見他,就知道是他了,果然他也發現躲在角落裡的她。她一直把自己裝作很低調,不讓任何人發現,可是他還是發現了她。於是她就跟了他回家,她確實有很多選擇,但活得太久太膩,她已經不知道是什麼時候放棄了掙扎,任由人們去安排她的生活。
從前她的夢想是環遊世界,乘飛機搭遠洋渡輪,看看其他地方是怎麼樣。可是去多了,久了,就想在一個地方停留下來。對她來說,她已活到那個去一個地方或一萬個地方都一樣的情景。如今她只想睡得穩穩妥妥,吃得飽飽滿滿,不再與任何人發生感情。
把我留在這裡,我不想去你的家。她想告訴他,可是他完全聽不明白她的話,一意孤行地把她帶走。她知道她又要策劃逃亡,應該是時候動身去找那夾在牆身的同伴*,又或者去看那把讀書文化人當作是傻瓜的傢伙**。這兩個小傻蛋,活得沒自己這麼久,名氣卻是響噹噹的。他們都比自己幸運,遇上讀書人,把他們寫進名著之內,不像自己,穿州過省,上山下海,最終只能目睹一個又一個將自己當作如珠如寶的人死去。
不過要逃亡,一切言之尚早。她要裝作跟自然規律配合,慢慢地淡出他的生活。突然離開,只會讓自己的大頭照片貼滿燈柱,她不想被任何人指責。她要靜悄悄地離開他,就約定三個月後吧!感情沒有建立得這麼深厚,分開後就不用太傷心,她不想學那活了一萬次的前輩***,每次都弄得對方哭哭啼啼。她是修道的,要積多點福。
她終於來到他的家,一個很乾淨卻又很混亂的家,滿室都是書,書櫃內、地上、床上,顯得很擠逼,卻又莫名其妙地潔淨。他騰出了空位讓她先睡,然後就說自己還要趕稿,不能陪她。她打了個呵欠,裝作很累地躺了下來,隨意問了他一句。你是一名作家嗎?是的。你會把我寫進書內嗎?當然會,我就是這樣子才把你帶回來。
他到廚房煲完水後,就默默地坐在書桌前。她又裝作跟他沒有任何關係,閉著眼詐作睡去。一閉上眼,往事就湧現在眼底,什麼偷靈丹,什麼修道成仙,什麼戰爭,什麼和平,她一一都經歷過。然後他又想起那同伴、那傢伙、那前輩,四個圍在一起聊天,真的挺高興。是時候動身,大約四十年前,她對世事無感,就停在這小島,奴才換了一個奴才,最終在幾個月來到一間寵物店。她看準這店生意淡泊,打算長遠,怎料又被一個奴才買下,真糟糕。
奇怪的聲音自廚房響起,打擾了她的冥想,應該是水煲滾的聲音。她以為他會去關掉爐頭,怎料過了一陣子他仍然沒有反應。她打開眼,看見他伏在書桌上睡了。現在的讀書人真是孱弱。她沒有別的選擇,只好跳到他的頭上。他醒過來,搓搓眼問:幹什麼?糟糕了,是水滾,你一定很驚慌了。
他匆匆跑進廚房。她嘆了口氣,看見一室都是書,電腦上密密麻麻的字,嘆了口氣:還是等你寫好這本書才離開吧,人類真是脆弱的動物。
*取材自愛倫.坡小說〈黑貓〉
**取材自夏目漱目小說《我是貓》
***取材自佐野洋子繪本《活了100萬次的貓》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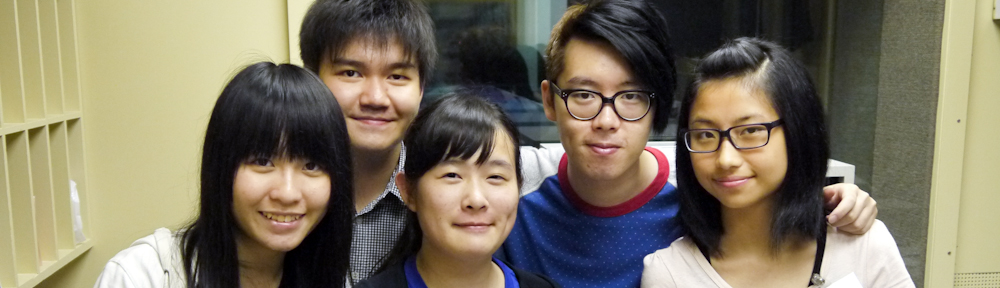
 「可不可以跟你做訪問?」「只是簡簡單單的,一會兒就好了。」「你曾經是風雲人物,你也想大家都知道你的過去。」
「可不可以跟你做訪問?」「只是簡簡單單的,一會兒就好了。」「你曾經是風雲人物,你也想大家都知道你的過去。」 「你昨天走得這麼快?」「我老了!」「別這樣說,誰不知道你當年是球場小旋風,差一點就踢到甲組⋯⋯」「你也懂得說當年⋯⋯還是不說了,我還要開會⋯⋯」「下一次再踢吧⋯⋯」
「你昨天走得這麼快?」「我老了!」「別這樣說,誰不知道你當年是球場小旋風,差一點就踢到甲組⋯⋯」「你也懂得說當年⋯⋯還是不說了,我還要開會⋯⋯」「下一次再踢吧⋯⋯」
